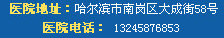原创牛汝辰
地名不仅反映社会的变迁,同时也反映植被的变化。自然环境对地名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有一些地名就直接以自然环境中的植物、植被等为命名对象。植物地名不仅直接呈现地域景观特征,其发展变化还反映地域的历史发展和形态演变。
所谓植被地名学就是研究地名与环境、地名与植物之间关系及其变化的学问。植被地名学又称植物地名学,植被地名学属于地理地名学或环境地名学的分支。
一、从地名看植被分布
如果将北京地区十万分之一地形图中的与植被有关的地名摘出,绘成一幅八十万分之一的北京地图,在我们眼前就仿佛出现了一张北京地区的植被图。在这幅图上,可以看到在北京西山和军都山的深山地区,其主要植被是松树、杏树、梨树、粟树、桑树以及樱桃等经济林木;在平原地区除桑树、杏树、枣树以及零散的柳、榆、槐等人工栽种的树种外,还有诸如苇子坑这样的沼泽盐碱植被类型。
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北京北部的军都山山地中有许多地名与松树有关,如平谷县有黄松峪,密云县有松树峪、松树掌,怀柔县有二松沟、南北二松树台,延庆县有松树沟、松树梁等。在北京的西山还有五里松、门头沟有松树、房山县有八里松等。它表明这一带历史上曾有过广大的松林。有关燕山南麓泥炭中所含的孢子花粉组成的研究表明,在离现在最近的全新世泥炭层上部,松树花粉含量一般高达90%左右,这表明燕山南麓的沼泽地带以及北部山区,是以松树占绝对优势的森林景观。在宋代黄裳制作的地理图中,沿着阴山山脉,绘了松树的符号,东段被称为“千里松林”。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明确地记载:“说者曰:居庸东去松林数百里,中间间道,骑行可一人,谓之扎八儿道。”可见元明时期居庸关以东数百里是连成一片的大松林。
又如北京西山地区,现在几乎没有原始林木的残存,但在地名上却保留着它们的影子,如昌平县的五里松林、门头沟区的松树、檀木沟以及房山县的八里松、檀港等地名,说明古代这里可能有过大片的原始森林。据文献记载,北京西山是盛产木材的地区。明代张鸣凤《西迁注》说:“西山内接太行,外属诸边,磅礴数千里,林鹿苍黝,溪涧镂错其中,物产甚饶。”元明时代,西山林木被大量砍伐。特别是元代修建大都宫殿、寺观、衙署、房屋等所用大量林木,多半来自附近山区,而西山一带正是采伐的重点地区。
地名还反映出这里混交性森林景观特征——既有温带落叶阔叶林,又有松林和高山针叶林。如在山地地区有许多杨树、柳树、榆树、椴树等温带阔叶树种为名称的地名,说明这些山地有大量温带落叶阔叶树生长,是温带针阔混交林。
在森林的平面分布上还可以看到,北面的山地,耐寒树种的地名,如椴木台、椴槐沟、椴木沟、柏木井等地名,较南面山地同类地名要多得多,说明北京北部山地较南部山地在树种上要更耐寒一些。
从北京山地地名还可以看到垂直分布变化。典型的例子如在京西房山县与门头沟区交界处有三座山峰,即百花山(高程米)、白草畔(高程米)、大黑林(高程米)。华北地区植物垂直分布的大致高度是米以下为落叶阔叶林,—米为针叶林,再上直到山顶为高山草甸。大黑山处于米,正好是针叶林分布的高度。而白草畔和百花山虽高度不到米。但因地处山顶、风势较大、降水不易保存等因素的影响,使之不能形成森林,而成为高山草甸。这在地名上也反映了北京地区森林植被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
在北京的浅山区有很多与经济林木有关的地名,如房山县的栗园、杏园、南梨园、梨村,门头沟区的东、西桃园、桑峪、栗园庄,丰台区的栗园、梨园,平谷县的桃园杏园、大果园,密云县的栗园、桃园、栗树园、桑园,怀柔县的桃峪、梨树沟,昌平县的杏树梁、桃峪沟、东、西梨园,里、外桃园,延庆的梨树湾、杏园、桑园、果园等。北京的平原地区,由于地处永定河、潮白河、温榆河等河流的冲积扇前缘地带,而且这些河流历来经常因改道而泛滥,因此在北京平原地区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沼泽及盐咸洼地,生长着芦苇以及盐生植物等。对此在北京平原地区的地名上也有反映,如北京北部的苇子坑,东北部的苇子坑,以及前、后苇沟等,通县南部还有熬硝营等。[1]
何小平、宋行标绘制了一张浙江嵊县的植被地名图,[2]收入余条地名。这幅地名图反映了嵊县植被的现实分布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嵊县地区植被在一些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变化。
在这幅植被地名图上可以看到嵊县米以上地区其主要植被为松科的马尾松、黄山松,杉科的杉木,茶科的茶树,壳斗科的麻栎,蔷薇科的桃树,竹类以及油桐、油茶、白术、木杓、葛藤等。米以下的丘陵地区则分布着马尾松、竹类、茶树、桑树以及零星分布的樟树,野生油类植物,野生麻类植物,山毛榉科的栗树,榆科的榆树,紫杉科的榧树,金缕梅科的枫香,紫葳科的梓树、苦楝、鸟柏、枫杨、柏、青梅、杨梅、李。中央河谷盆地除茶、桑、桔、竹类地名较多外,尚有零星分布的杨、白杨、柳、乌榆、梅树、桕树、梓树、枫树、枣树、荔枝树、梨树、柿树、麻之类植被的地名。低洼处则有与荷花、莲子、藕以及菱有关的地名。
在这幅地图上还可以看到嵊县山西有不少地名与松竹有关。如奖山乡的松树岭,通源乡的松明暗,竹溪乡、城溪乡的竹山,石璜区的水竹塘、后白竹,长乐区的油竹潭、苦竹,南山区的淡竹园,里东区的箭箬岭等。历史上有关松竹的记载也比较多,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嵊山临江,松林森蔚。”嵊县的竹类地名甚多,这说明了历史时期竹类在此处有分布。在有关嵊县植被的历史记录中,当年占优势的毛竹今天并未占有多少优势,相反却以野生竹类箭竹等居多。
《剡录》引《尔雅》曰:“东南之美,有会稽之竹箭焉。”竹箭即竹。嵊县现存的竹箭类地名也比较确切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即竹类地名以箭竹类居多。其他野生竹类古籍记载也颇多,故嵊县现存尚有苦竹、油竹、水竹等地名。杉树也是嵊县植被的主要树种,主要分布于丘陵山区,以长乐、北山、里东为多。嵊县的杉木地名分布比较符合这一范围,如长乐区的杉树湾,里东区的大杉树以及崇仁区的树杉杉湾等。另外茶树遍布全县,为山区、丘陵的重要植被。此县有关茶的地名反映了茶的生长、采摘、烘焙及制成的过程。如茶草湾、盘茶、茶亭岗、茶坊、茶培。
华蓥山很多地名是以植物名称或以生态特征命名的,且与海拔高度、部位、土壤类型极其吻合,留下了古代自然面貌的痕迹。中上部为石灰岩山地,矿子黄泥土广泛分布,曾经生长着大量喜中性偏碱的植物,于是有马桑湾、楠木顶、樟树湾、椿木坪、白竹凼、山竹碑、方竹坪等地名,据考有的地名出现在数百年之前。在山的下半部,基岩为砂岩,在其发育而成的酸性砂壤上,又覆盖着与之相适应的松、杉等植物,始有松树林、松树坡、丝栗坡、酸枣坪、大竹林等地名。山区农耕区中,也有檬子、凉山树、桐子湾、桐子排、柏木湾、板栗湾等以树种命名的村庄。山脚深丘地带,宜于发展经济林木,因而出现梨园沟、李子坡、柿子坪等村名。
与地名相互印证的各县县志集中说明了原先这里环境良好,森林茂密,古木参天,浓阴覆地,以至“曲径碧苔封”。令人痛心的是,这些迷人的景象已经消失了。入山采访,只有历史上留下的美名能唤起人们对昔日蓥山的遐想。[3]
二、从地名看植物变化
据《北京地名典》等史料记载确定其中条植物地名出现的时间,并将其历史形成过程划分为金元时期(阶段1)、明清时期(阶段2)、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前(阶段3)、改革开放后(阶段4)这4个阶段。根据《北京地名典》记载,在金代到元代的历史时期中,有潭柘寺(金)、柳林馆(辽)、高粱桥(元)、垂杨柳(元)等植物地名出现,零星分布在城址内外,无明显规律。从阶段2开始,植物地名逐渐增多并逐渐聚集在城市中心,空间分布仍较为分散。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出现的植物地名密集分布在中心城区,多达条,是4个阶段中新地名出现最多的时期。而改革开放后,新增的植物地名明显减少,仅有37条,并高度集中于西便门至崇文门一带。[4]
地名的增长变化与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前,碍于有限的文献记载和尚未成熟的地名规划,大量地名未能流传使用。清代以前,地名管理工作围绕行政地名展开,体现当朝统治者的意志。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管理者以地名规范化为要求,进一步推进地名管理工作。植物地名受年北京街巷胡同名称整顿影响形成地名系列化现象,其中以槐树街为词源的地名,从槐柏树街北头条至十条、槐柏树街南头条至十一条,总计达21条。再如根据桃杨路3条支路位置不同,将其分别命名为“桃杨路头条”“桃杨路二条”“桃杨路三条”,不仅规范管理,也丰富了植物地名的分布。
除此之外,自20世纪90年代城市危改速度加快,大规模街巷胡同被拆除,致使植物地名成片消失,也导致阶段4植物地名增长率下降。该阶段北京东西城区拆除和部分拆除的街巷地名总计条,其中植物地名消失共计93条。这些植物地名有68条集中在旧城区,25条分布在新城区,得以幸存的地名也迫于城市建设需求难以避免其实体景观消亡的结果,其中旧城区“名存实亡”的植物地名成组团分布,主要集中于西城区西南部广安门、前门和南二环天坛南部。[5]
敬请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yf/1117.html